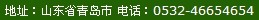|
克白灵苏孜阿甫片 http://m.39.net/pf/a_4340651.html 文 冯尚鉞 编辑 杨轩 李炳南有一个特殊身份。这个放学后通常坐在深圳一家旧货店,给家里帮手的懂事小孩,也是街坊人人皆知的“电脑高手”。 李炳南在9岁时,已经在少儿编程App“编程猫”的社区里,发布了94个作品,收获3.6万次浏览和个赞。 他还做了其他一些成熟程序员的工作:他为社区撰写了大部分的源码图鉴,帮助其他孩子学习使用编程。他用编程猫提供的模块模拟出了《植物大战僵尸》,这个用半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具有非常高的拟真度。他甚至在班上和社区里还有自己的一批“程序员徒弟”。 这始于一件小事:有一次,李炳南和妈妈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玩具店里,其他孩子正在在玩乐高,李炳南站在那里一直看他们玩。他妈妈问他要不要买,李炳南却说“我不想买,我看看,我看得懂里面是怎么回事就行。”回家后,李炳南用家里的电脑画图,把记忆中的乐高部件一件件画下来,再用画图工具“拼装”。 在一次分享活动中,流塘小学的叶滨洁老师注意到了这个孩子的画图作品。他不相信这是9岁的孩子用画图软件做的,于是他去家访。发现他家的电脑“已经老得不能用了”。叶老师察觉到了孩子的天赋,帮助他接触并安装了编程猫,甚至自掏腰包给李炳南家送了一台主机。 在叶老师和“猫老祖”(编程猫中的一个核心角色,负责对孩子提供指导)的鼓励下,李炳南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下课完成作业后,他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编程学习上。 一开始,李的妈妈并不理解编程,也不明白编程教育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支持孩子的兴趣以外,最大的理由是因为电脑在家里,可以防止孩子到外面闲逛,被社会上的人带坏。她曾经眼看到几个周围的孩子被人引诱,染上了“止咳水”的毒瘾。 但事情已经今非昔比——如今的李的妈妈如今已经成了编程教育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她接受采访时有些腼腆,甚至谦称自己是个“半文盲”。但她如今已经可以肯定“搞不好这个编程这个东西,会成为像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必须的(技能)”。 有人质疑“编程教育是否太早”,她则会引用奥巴马和邓小平的话加以反驳:“奥巴马都很重视编程,他们国家六岁的孩子编程也可以玩的很好。邓小平也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他们都这么说了,证明(少儿编程)应该是可以的吧?” 编程猫“少院士”李炳南的获奖证书 2 李炳南妈妈的印象是对的。奥巴马的确推广过编程,在年的“计算机科学教育周”(CSEW)开幕当天,他用一小段JavaScrip代码成功地在屏幕上画出一个正方形。 奥巴马还邀请了20名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南十七街学校的学生来到白宫,与他一起学习“编程一小时”的课程——这一项目旨在让学生在一小时内学习到基本的编程知识。奥巴马说:“如果我们想让美国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掌握这种工具和技术,它将改变我们所有的做事方式。” 美国硅谷的兴盛,往往使得人们以为,在美国早已实现了编程的普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Code.org的调查,美国有十分之九的学校没有开设计算机科学课程,计算机教师的匮乏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一头,其实比起70、80年代的少年极客在电脑前查阅Basic语句或汇编代码,用电子元件DIY芯片,在年前后,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的开源编程教育工具已经逐渐完备。例如图形化的少儿编程工具Scratch、电子开源平台Arduino、教育型机器人VEX等的教学案例、设备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并且拥有了数百万成员的用户社区。 就这样,需求的迫切,工具的完善,加上资本和政府力量的推动,促成了年后全球范围内面向少儿的编程教育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波浪潮中看到了机会。 编程猫的联合创始人孙悦正是其中一员。他正在芬兰进修深度学习,一次他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同学李天驰参加一个互联网峰会,看到一群当地孩子在会场编程,水平甚至高过了很多国内大学生。他想起自己在北欧所看到的经历: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已经将编程纳入了小学必修课,加上他们二人很早学习计算机的经历。他们产生了一种感觉:这里可能存在机会。 他们会学校后开始搜索,想看看作为IT大国的中国有没有一个像新东方学而思一样有实力的少儿编程教育机构,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一个也没有。李天驰和孙悦,将自己的编程教育思路整理后,报名参加“傅盛战队”创业孵化比赛,进入了前二十强。在“想了一二分钟”以后,他们俩作出了一个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创业。 在进行了几个月的调研和摸索之后,李天驰和孙悦正式注册了公司开始运营。一开始公司人手只有他们二人,还没有成型的产品,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们在
|
时间:2023-4-1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游戏是儿童的语言,父母要玩给他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