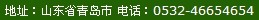|
“我们必须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在我们的内心寻求它们……”——卡尔·荣格 卡尔·荣格是西方心理学巨擘,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年)。而藏传佛教诞生在世界屋脊雪域高原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时间上更有着近千年的差距,它们之间怎么对话?有必要对话吗?人们不禁要有疑惑。然而,美国的拉·莫阿卡宁却坚信在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这两种体系之间必定具有某种深刻、重要的联系。在他看来,藏传佛教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心理学和伦理体系,而藏传佛教密宗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过程,“它在我们深切向往象征性和精神的神秘性,及我们需求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始终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置身生活之中”。这么一来,就和卡尔·荣格一生致力研究的意识扩展和精神转化过程的论题便有了最直接的联系。于是莫阿卡宁“开始了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的令人激动的漫游”,并且在几年的漫游之后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本书——《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在书中,他力图证明藏传佛教徒和卡尔·荣格各自从他们独特的方向,用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象征向我们一致表明:智慧是普遍的,排斥丰富的西方象征,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和损失。然而,东方的象征对西方人的心灵来说更为新奇,从而也具有更大的激发和刺激想象的能力。这在藏传佛教热浪冲击西方神学体系的今天,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时间、空间上的差异并没有损害藏传佛教和荣格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于是才会有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而西方世界的人们也能从这两种体系慷慨奉献的财富中各取所需,汲取无穷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你能说这种对话不值得吗?在这里我们不想介绍太多的索然无味的名词、概念,力图以普通的语言来介绍两种体系的对话。一方是藏传佛教的朱古(活佛),一方是卡尔·荣格的徒子徒孙,旁白则非拉·莫阿卡宁莫属了。对话的主题则是关于痛苦和解脱痛苦的方法。我们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是世间众生最普遍关心的问题。莫阿卡宁:对话一开始就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两者针锋相对,对痛苦是否能被超越发生了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真诚的交流。朱古:并非罪恶,而是无明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佛教最关心的是消灭痛苦,因为它相信痛苦实际上是可以被超越的,摆脱痛苦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荣格:我完全赞同你所说的无明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按我的说法,这是因为自我认识的贫乏,使得人们被无意识的冲动所奴役。但痛苦是生活的本来状态,甚至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除的必要元素。人们必须面对痛苦的问题,痛苦又必须被克服,而克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忍受它。朱古:藏传佛教认为痛苦是可以被转化为欢乐的。虽然说在到达最终目的地的过程中绝不是没有痛苦,功德高深的修行者也可能要经受各种痛苦的考验,但其最终的结果必是极乐。荣格:很遗憾,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痛苦和欢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组对立面,没有一方,另一方也就无法存在。为了保持生活的圆满和完整性,需要有欢乐和痛者之间的平衡。痛苦是自然的,不是生活中的病态;欢乐只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状态。朱古: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重要。佛教所迫求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人类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想来在这方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荣格:一点不错,医治人类精神的创伤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工作。为此,我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走出了一条精神疗法的路子。我的精神疗法不仅仅是对病症的治疗,更重要的是实现个体的完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切未来发展的种子,我的任务便是帮助这颗种子发展、成熟,直到发挥它的最佳潜能。朱古:你的精神疗法和佛陀的体验如出一辙,佛陀用他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直接体验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赋予生命的价值。同时,也只有通过发展菩提觉,即绝对的、无限的、超自然的意识,在人自性中的亲证,我们每个人才能寻求到根本存在的问题的答案。莫阿卡宁:换句说法就是,我们既没有必要到遥远的、神秘的地方去寻找它,也没必要从书本或者圣典中寻找它,只需在一个人自己的灵魂深处寻找它,也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它。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荣格:听其自然,这是最好的敲门砖。我仔细观察过那些成功地摆脱生活问题缠扰的患者,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简单地顺其自然,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允许自己的无意识在寂静中和他们交谈,他们耐心地倾听它的信息,并给予它们最大的和最认真的西宁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白癜风的医疗
|
时间:2016-12-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钢琴学习入门之识谱及基础乐理
- 下一篇文章: 献给韩语学习者韩语入门教材大推荐